
最近拜读了一位家世显赫的紫砂才女的文章,深受启发。但其中反驳徐鳌润老先生的关于“南山”位置和“金沙寺”的观点,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之前已经撰文阐述了我对南山位置的看法(“思向南山拾堕樵”——南山到底在哪儿?),今天继续来聊一聊金沙寺。
才女的原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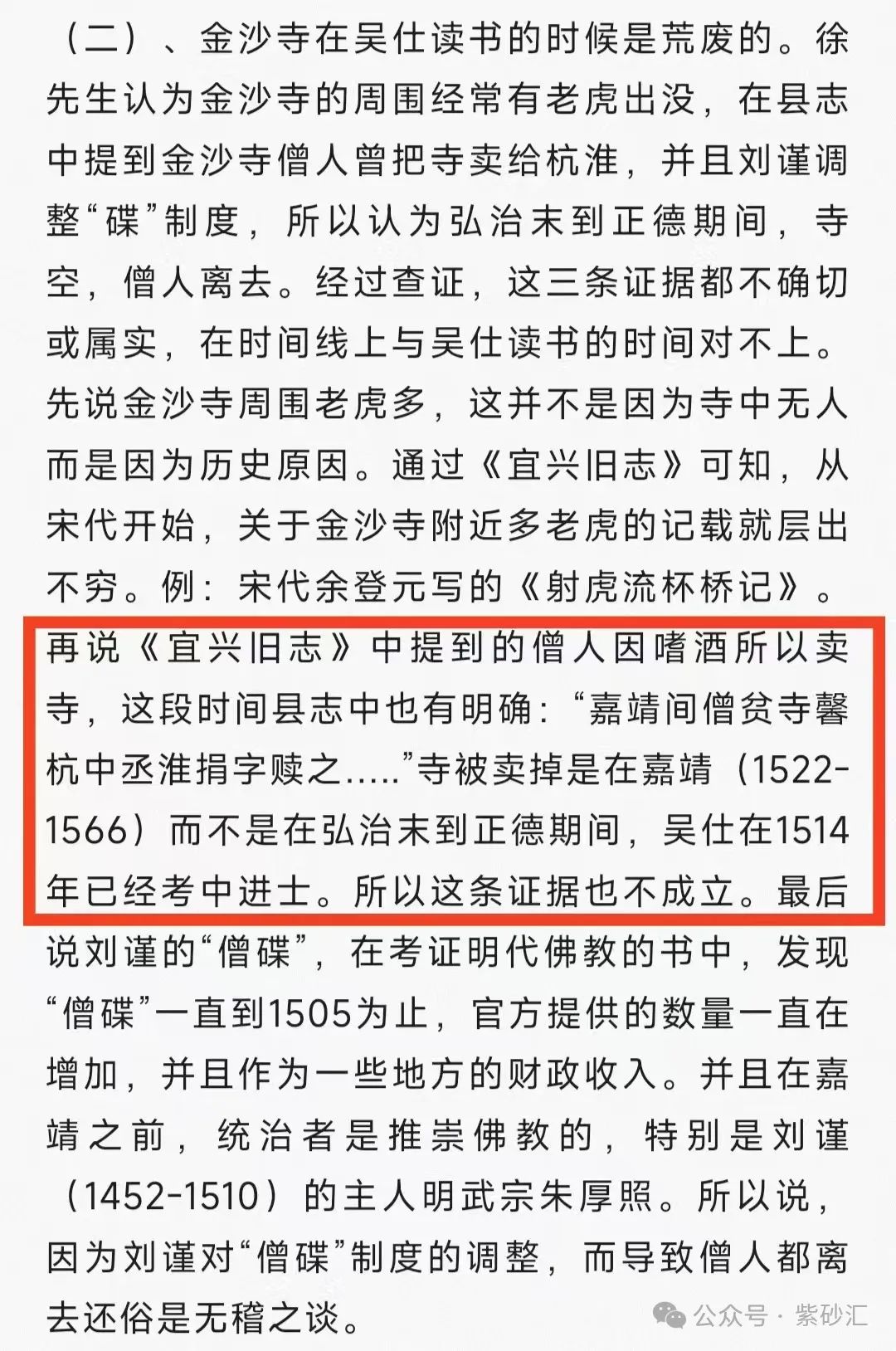
按照常理,“寺中无人”的原因是“老虎多”,而非反之。老虎多了,香客不来烧香,和尚也无所事事,只能另谋出路,这才符合逻辑。谁也不会违背常识地认为“老虎多”的原因是“寺中无人”。
但是,这不是重点。
再说僧牒的事。太监刘瑾严查僧牒,这是历史事实。才女查到的资料,嘉靖之前崇佛,这当然也是事实。至于当时的僧牒数量有没有增加,我没去考证,姑且就按照才女的考证结果:整个社会的僧牒总体数量增加了。但这又怎样?全社会的合格僧人增加了就代表不合格的僧人也不怕严查了——这是什么逻辑?增加的僧牒是颁发给合格的僧人的,严查的是不合格的僧人,这矛盾吗?金沙寺僧,县志都记载了“嗜酒”,属于破了酒戒的不合格僧人,不正是被严查的对象吗?此时不跑路更待何时?等着被湖㳇群众举报吗?
但是,这也不是重点。
重点是金沙寺有虎患且非常破败荒凉的这一段时间跟吴颐山读书的时间是吻合的。
徐鳌润老先生着重提到而才女只字未提的一本书《荆溪疏》才是本文的主角。
《荆溪疏》刊刻于万历十二年(1684年),名为“疏”而实为“志”,具有纪游、纪事、纪实的特征,其性质和作用与方志无二,可信度非常高。
作者王穉登,苏州人,是当时著名的文人和书法家,文征明弟子。曾两次来到宜兴游历,一次是嘉靖四十年(1561年),另一次是万历十一年(1583年)。在所有明代到宜兴游历的文人中,王穉登是逗留时间最长并专门写了游记记录的。
《荆溪疏》记其游金沙寺经过云:“寺左有杭中丞祠堂,弘正間諸髠嗜酒,悉賣寺田,中丞出鍰贖其半,歸常住,故没而俎豆其中。”弘正间就是弘治、正德年间,髠是秃子的意思,此处指和尚。意思就是在弘治、正德年间,金沙寺的和尚因为嗜酒,已经开始变卖寺产了。
才女认为寺被卖掉是嘉靖年间的事,但她引用的这段话“嘉靖间,僧贫鬻寺,杭中丞淮捐赀赎之”(清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讲得清清楚楚,嘉靖年间的杭淮是把和尚(陆陆续续)卖掉的寺产赎回来,再捐给和尚。也就是说,“卖寺产”这个事,是从弘治一直持续到嘉靖的,而终结这个事的人是杭淮。但即使是在杭淮出资重建后,金沙寺也依然荒凉,这是后话。
那么为什么在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这漫长的岁月中,金沙寺都如此荒凉破败呢?不光是因为和尚嗜酒,虎患才是根本原因。自晋而后千余年间,金沙寺附近山中猛虎繁生,虎患从未间断,尤以明代为甚。嘉靖四十一年(1562)王樨登亲临金沙寺,记其行程:“蜀山折而南可二十里,曰湖没······地多虎,白昼咥人,暴甚。一岁中死者几二千,指近虎妖也。余同幼元来游。先三日,射杀一虎。巡检藏其皮,俟县官入计还,受赏格。肉作醢售之,饲小儿,能稀痘。”万历十一年(1583)王穉登再临金沙寺:“余以万历癸未闰二月初二,间道走金沙,路中见虎迹。舆夫尽怖。幼元命举炮震山谷。然闻山人言,虎惊则跳而噬人。即入寺,舆夫指所从间道(由玉女潭行)者,虎穴也,不寒而傈。”一年之中吃了1000多人的老虎在出没,官府在悬赏,这样的地方,老百姓敢去吗?没人去香火能旺吗?
吴颐山读书,一般认为是在正德三年(1508),杭淮赎回重建金沙寺是在嘉靖十四年(1535),那时吴颐山已经退休。而在杭淮赎回重建金沙寺之前,《荆溪疏》等众多史料证据都指出:金沙寺有猛虎为患,几乎没有僧人,十分荒凉破败。请问,换做你,你会选择在这么一个鬼地方读书吗?
当然,书还是要读的。
作者后记:从古至今,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托伪”现象。比如《黄帝内经》显然不可能是黄帝写的。李亦畲在《太极拳跋》中说到:“此谱得于舞阳盐店”,当代学者研究后认为,“舞阳盐店”也是一个虚假的地理信息。同样道理,紫玉金砂——多么工整的对仗啊,寺名金沙是巧合吗?金沙寺很可能也是一个托伪的紫砂起源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