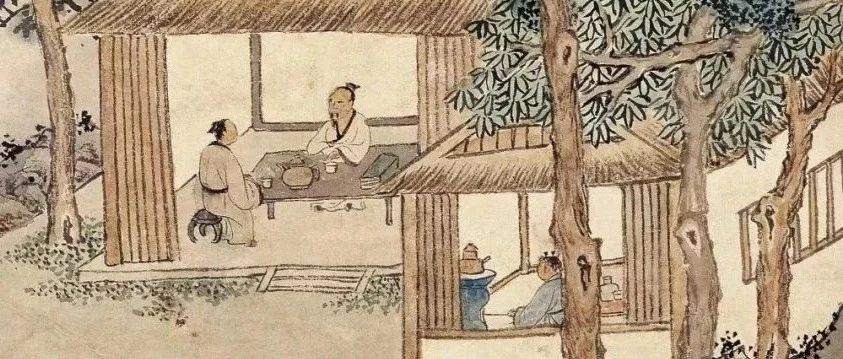关于紫砂壶的起源,目前有两种观点:一是明末周高起《阳羡茗壶系》“金沙寺僧传供春说”;一是清初周容《宜兴甆壶记》、吴梅鼎《阳羡磁壶赋》“供春大潮山澄泥为壶说”。尽管多数人持前种观点,但是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供春大潮山澄泥为壶说”的可能性更大。
大潮山澄泥为壶说,并非今人的凭空杜撰,也不是部分研究者所认为的已故文史学者徐鳌润提出的观点,而是有较为可靠的文字记载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认同这一观点,因为其佐证材料更合乎情理。
其一,观点源于史料。清顺治十一年(1654),浙江鄞县(今宁波)诸生周容游宜兴,“询壶之所自来”,写下紫砂史上第一篇详细介绍紫砂壶制作技艺的文章《宜兴甆壶记》:“今吴中较茶者,壶必言宜兴瓷。云始万历间大潮山寺僧传供春。”信息源自吴梅鼎和许龙文,“甲午春,余寓阳羡,主人(吴梅鼎)致工(许龙文)于园,见且悉工。曰僧草创,供春得华于土,发声光而已”。同年,吴梅鼎因“有客(周容)过阳羡,询壶之所自来,因溯其源流,状其体制,胪其名目,并使后之为之者考而师之。是为赋”,写下紫砂史上第一篇优美的文赋《阳羡磁壶赋》:“余从祖拳石公读书南山,携一童子名供春,见土人以泥为缶,即澄其泥为壶,极古秀可爱,世所谓供春壶是也。”吴梅鼎的溯源有家学传承,其父吴洪化,字以藩,是紫砂壶的收藏家和鉴赏家,值得信赖。《阳羡磁壶赋》曰:“先子以藩公嗜之,所藏颇伙,乃以甲乙兵燹,尽归瓦砾。”周高起《过吴迪美朱萼堂看壶歌兼呈贰公》曰:“吴郎鉴器有渊心,尝听壶工能事判。再三请出豁双眸,今朝乃许花前看。高盘捧列朱萼堂,匣未开时先置赞。卷袖摩挲笑向人,次第标题陈几案。每壶署以古茶星,科使前贤参静观。指摇盖作金石声,款识称堪法书按。某为壶祖某云孙,形制敦庞古光灿。”
其二,南山即大潮山。《阳羡磁壶赋》曰“余从祖拳石公读书南山”,此南山即大潮山。纵观历代宜兴县志,虽然南山多数为泛指,但确有所指的是大潮山。明正统间武进王俱《南山十景诗序》云:“去宜兴东南五十里有山,名大潮山,以其在县城之南,故又名南山。”清乾隆间海宁吴骞厘补《阳羡名陶录》按曰:“大潮山,一名南山,在宜兴南,距丁、蜀二山甚近,故陶家取土便之。”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曰:“大潮山,一名南山,在县东南五十里,上有金鸡墩,内有洞,可容纳二三十人。”
其三,吴仕有缘读书南山。凡事得有个缘由,既然吴仕读书南山,那么吴仕为什么会读书大潮山?据济美堂《吴氏宗谱》记载:“(吴仕)自幼警颖不群,甫冠,历游诸名彦门,闻识益广。”明代黄渎沈氏为宜兴名门望族,元季避乱自吴兴迁居黄渎,始迁祖代州公沈茂,传松隐公沈荣,再传户部公沈彝。正统甲子(1444),沈彝自黄渎迁居大潮山麓,建祠堂曰“渊源堂”;山上植松万株,山下建楼名万松楼,其成宜兴古名楼之一。宜兴吴氏与黄渎沈氏关系密切。吴仕伯父吴经、父亲吴纶皆宜兴名士,沈彝与他们颇有交情。沈彝子沈曦之长女嫁于吴经长子、南京礼部尚书吴俨。沈彝子沈晖官南京工部右侍郎,致仕后协助吴经将久废的东坡草堂从百姓手中赎捐而扩建为东坡书院,将四女儿嫁于吴仕的胞弟吴佶。吴仕“甫冠”(20岁),值沈晖由南京工部右侍郎致仕,弘治十四年(1501)又值乡试年,故吴仕游历于大潮山麓,借宿大潮福源禅寺,读书于沈氏万松楼,早晚请教于沈晖。时间、地点及事情的缘由,符合人物年龄和实际情况,吴仕读书南山的时间应为弘治十三年。且大潮山有奇胜,明初为“南山十景”之一,山上福源禅寺“入山不见寺,深在万竹中”“坤与秀气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也是文人墨客经常造访之处。可见吴仕读书的南山是指大潮山。
其四,沈晖与吴仕关系密切。这更可佐证吴仕读书南山,吴梅鼎所记“余从祖拳石公读书南山”非虚。沈晖与吴仕的密切关系在《颐山私稿》中斑斑可见。正德十三年(1518)九月十五日,沈晖卒于家中,吴仕供职礼部,闻讯特作《祭沈亚卿文》遥祭:“嗟乎!古人有言,艺不两能,法家文苑,爱焉异称。公善为文,尤长吏治。古所未能,至公而备。郎署藩方,台丞卿佐,茂绩蜚声,所在而播。中更物议,乃疏乞休,人实公忌,于公何尤。优游林下,几于廿年。诗囊书笥,绿野平泉,有美一丘,公所自营,曰凰川里,于焉永终,有禄有年,有孙有子。凡今之人,孰与公齿,公死无憾,我心若遗,于何考德,于何质疑。某也无似,辱爱至厚,瓣香未持,罪在不宥。南天遥遥,寄此短章,溪毛涧芷,公其来尝。”沈晖下葬时,吴仕为其撰写了《明故南京工部右侍郎进阶资善大夫豫轩沈公行状》。沈晖生于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吴仕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两人相差43岁,是真正的忘年之交。吴仕“甫冠”前,沈晖在外为官42年,与吴仕接触不多,致仕后得以对其言传身教,忘年之交日切。吴仕之博学颖悟,甚得沈晖之喜欢,沈晖本想将四女儿嫁于吴仕,无奈吴仕已有婚约,最终沈晖将四女儿嫁给了吴仕的胞弟吴佶。吴仕“甫冠”不久即娶妻生一女,若不是“甫冠”之年读书大潮山,又何来沈晖欲将四女儿嫁于吴仕一事呢?
其五,地域环境适宜创制紫砂壶。紫砂壶不可能无端地就出现,它的出现应与当时生产环境有关。大潮山及与之相连的东山(黄泥场)、白泥山、凤凰山等蕴藏着丰富的陶土资源。自明清至民国,乃至改革开放前,丁蜀陶业所需70%的陶土原料都出产于此。陶土开采历史悠久,东山甲泥矿、白泥山白泥矿、凤凰山甲泥矿分布在大潮山麓附近。山麓傍河处曾是堆晒陶土和淘洗陶土的场所,黄泥场、白泥场等村名都因此而得。丁蜀窑场兴起于明代,明之前窑场则散布于南部山区傍河处。洑东村窑头自然村因窑而得名。白泥场自然村既是泥场,也曾经是窑场。涧众唐代古龙窑遗址,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此生产环境,便于“与陶缸瓮者处”“澄泥为壶”,其他地方则无此便利。且沈氏万松楼与大潮山麓淘泥场相距仅300米左右。吴仕白天读书于万松楼,自有沈家仆人伺候,小书童无事可做,与沈家群小去家旁泥场玩耍,随便抓把泥,揉捏出几个陶塑或“澄泥为壶”,顺理成章,合乎情理。虽说周容所记为“大潮寺僧传供春”,但吴梅鼎所记“(供春)见土人以泥为缶,即澄其泥以为壶”可能性却更大。据此,供春则于弘治末创制紫砂壶,正德间成为名工,紫砂壶遂为世人传用,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
金沙寺僧传供春说,是目前多数人所持的观点,源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然《阳羡茗壶系》只载吴仕读书金沙寺,却没有给出理由。后世研究者给出的理由,均源于吴骞《阳羡名陶录》所“按”内容的自圆其说,其论据乏力。吴仕无理由去金沙寺读书。
其一,紫砂壶诞生前后,金沙寺已十分荒凉。据宜兴旧县志记载,紫砂壶诞生前后的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年间,金沙寺十分破败。明弘治间邵珪《金沙寺》云:“酒酣欲访金沙寺,落日荒荒漫欲休。闻说希声读书处,榛荆满地白云秋。”王穉登《荆溪疏》记其游金沙寺经过云:“弘、正间诸髡嗜酒,悉卖寺田。”清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云:“嘉靖间,僧贫鬻寺,杭中丞淮捐赀赎之,其子颐泉、孙子宣拓成先志,复给田山屋宇,延僧圆珂居守,县令方金湖为肖中丞像,署额于内。隆庆六年(1572),重建殿宇,僧真寂延宝山庵僧德汾协力募成。”即便是重建后,金沙寺也依然荒凉。万历间任明铉《金沙寺》云:“闻道金沙苦行僧,披荆斩棘挂禅灯。荒凉古刹人稀到,咫尺红尘隔万层。”金沙寺显得荒凉之时,大潮山福源寺却香火旺盛,弘治十五年(1502)沈晖为之勒石题跋立碑。问题是吴仕缘何要去凄凉的金沙寺,而不去风景秀丽、香火旺盛的大潮山福源禅寺读书呢?若吴仕果真读书金沙寺,凭吴家之富,定会捐赀修缮,而不至于僧贫鬻寺。
其二,猛虎为患乃金沙寺荒凉之因。自晋而后千余年间,金沙寺附近山中猛虎繁生,虎患从未间断,尤以明代为甚。明正德三年(1508),即众人认为吴仕因母丧守制而读书金沙寺的那年,山东提学副宪邵贤致仕,于周孝侯祠旁建东邱娱晚楼,仿兰亭集会,邀沈晖参加。沈晖因风阻荆溪,泊船周孝侯祠旁,作诗,自注曰:“阻风溪上,谒周孝侯祠,就新建娱晚楼。时南山多虎,民有忧色。”嘉靖五年(1526)春,常州府责令宜兴县悬榜捕虎,榜出三日即捕一豹二虎。吴仕特作《擒虎歌》以颂。其诗序曰:“嘉靖丙戌(1526)春,侍御朱公按部宜兴,泽生苏枯,惠化既浃,剔蠹搜奸,闾里为靖,维兹虎患犹未殄息,膏流血溃,实用兴衰。乃下令国中,召猎徒悬赏,格戒时日,期奸厥类乃已。于是山鬼效灵,武夫用命。未旬,殪玄豹一白额虎二,相继以献,欢声载道,膏泽若流,乃作是歌,爱纪其实。”嘉靖四十一年(1562)王樨登亲历金沙寺,记其行程曰:“蜀山折而南可二十里,曰湖没······地多虎,白昼咥人,暴甚。一岁中死者几二千,指近虎妖也。余同(吴)幼元来游。先三日,射杀一虎。巡检藏其皮,俟县官(令梁诠)入计还,受赏格。肉作醢售之,饲小儿,能稀痘。”万历十一年(1583)王穉登再历金沙寺曰:“余以万历癸未闰二月初二,间道走金沙,路中见虎迹。舆夫尽怖。幼元命举炮震山谷。然闻山人言,虎惊则跳而噬人。即入寺,舆夫指所从间道(由玉女潭行)者,虎穴也,不寒而傈。”王世贞《玉女潭诸游记》亦云:“其(玉女潭)右为虎窟,人兽骨甚多,募猎士逐之去,亭其上。”猛虎为患,致使香客却步,寺院凄荒,寺僧无以为继,只能靠变卖寺产度日。
其三,“杭淮乃吴仕之师,杭淮捐赀赎金沙寺,故吴仕读书金沙寺”依据不实。据《颐山私稿·奉寿大方伯泽西先生八十序》可知,吴仕的老师,是杭淮的堂兄杭济(宜兴分水人),人称泽西先生,而非杭淮。杭淮,字东卿,明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嘉靖十三年(1534)致仕。杭淮捐赎金沙寺为嘉靖十四年之事,此时紫砂壶问世已多年,吴仕也已致仕,何以携供春读书金沙寺而创制紫砂壶呢?清嘉庆六年(1801)重修金沙寺,文渊阁校理、翰林院侍读学士、邑后学吴廷选撰《重修双溪公祠堂记》曰:“前明杭中丞淮尝读书湖㳇之金沙寺······”
其四,“吴仕因母丧守制而读书金沙寺”于情理不合。正德二年(1507)吴仕参加乡试考中解元,正德三年(1508)吴仕本应该赴京参加戊辰榜会试,却未能成行,所以有人认为吴仕是因母丧守制而读书金沙寺。殊不知按封建礼制,父母去世,孝子必须守制两年零三个月(共27个月),其间必须停止一切社交及娱乐活动,在家或筑庐于坟墓旁守孝,不得外出。吴仕既然考中解元,便不可能会做出有违礼制的事。既然失去参加戊辰榜会试的机会,下一次辛未(1511)榜会试还有三年时间,吴仕又何必要违制而急于读书金沙寺呢?
其五,“吴仕因读书金沙寺,故自号颐山”太过勉强。金沙寺所在之山,最早为无名之山,因唐昭宗时宰相陆希声退隐读书于此,见群山在上,罨画溪、太湖之水在下,乃《易经》“颐卦”之象,故取名颐山。据此,有人认为吴仕因读书金沙寺,故自号颐山,而实际情况是吴仕因精于易学而自号颐山。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轶闻》曰:“颐山历官学政,预决魁元,十不失一。河南尚维持父以事系狱,维持侍父囹圄,不得就试。按君某来监临,问颐山曰:今科举子何人?答曰:无出尚维持之右。按君查册,尚无名,即行牌提取应试,迨发榜,尚果第一,联捷。”“预决魁元,十不失一”,济美堂《吴氏宗谱》也有记载。
既然吴仕无理由读书金沙寺,而又有资料可证吴仕读书大潮山,紫砂壶为“金沙寺僧传供春”一说就更值得质疑了。或许是因为金沙寺颓败,寺僧无以为继,金沙老僧投靠香火旺盛的大潮福源禅寺,在大潮山创制紫砂壶,再传给供春。
为了进一步探明紫砂壶的起源,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清楚:
第一,紫砂壶究竟起源于何时?有人依据羊角山遗址的发掘情况而认定宋代就有紫砂壶。然经南京博物院陶瓷考古学家宋伯胤科学考证,羊角山遗址为明代窑址,而非先前认定的北宋窑址。山东博物院原院长张从军参观了羊角山遗址的出土文物后也这么认为。这也得到了中国宜兴陶瓷博物馆的认同。目前羊角山遗址出土文物的时间均已纠正为明代。据考证,自五代开始,宜兴陶业已由丁蜀南山转向宜兴归径一带,明代丁、蜀山陶业才兴起,且丁、蜀山至今未发现宋代窑址,紫砂壶起源于宋代无依据。所有的文字记载(包括《阳羡茗壶系》)都表明紫砂壶起源于明武宗正德年间。最早记载的并非《阳羡茗壶系》,而是明代大收藏家项墨林辑录的《项氏历代名瓷图谱》:“宜兴一窑出自本朝武庙之世,有名工龚春者,宜兴人。以粗砂制器,专供茗事。”此段文字写于万历十八年(1590)之前,比《阳羡茗壶系》早了50多年,很多人却常常忽视了这段文字记载。
第二,供春和朱昌是同一人吗?很多人认为供春就是吴仕的家仆朱昌,其实不然,供春和朱昌并不是同一个人,济美堂《吴氏宗谱》(卷首三·附义叔传)中供春和朱昌分别有传。不过,很明显,《吴氏宗谱》中的供春传是供春在被社会普遍认同为吴仕书童和制壶名工后,吴氏重修家谱时增加上去的,其内容主要摘自《阳羡茗壶系》,早期的济美堂《吴氏宗谱》未为供春列传。供春实有其人,相传姓龚,名春,为早期制作紫砂壶的名工,《项氏历代名瓷图谱》早有记载。至于“供春”是人名,抑或是茶名,怎么理解都可以。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凡留传后世刻有“供春”款的紫砂壶,均非龚春本人传器。
第三,成书在前就算定论吗?《阳羡茗壶系》成书于顺治二年(1645),《宜兴甆壶记》《阳羡磁壶赋》写于顺治十一年(1654),前者成书在前,且比后二者早了10年,是否前者就是定论呢?《阳羡茗壶系》成稿不久,周高起即被清游兵所杀,书稿为其弟周荣起收藏。《阳羡茗壶系》何时刊印成书,情况不清。目前所见最早的单行本为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王晫、张潮所辑“檀几丛书本”。尽管《宜兴甆壶记》《阳羡磁壶赋》成文时间晚了些,但可以肯定的是周容写《宜兴甆壶记》、吴梅鼎写《阳羡磁壶赋》时,都没有读过《阳羡茗壶系》。否则,就没必要再“考而师之”。且《宜兴甆壶记》《阳羡磁壶赋》并不是在《阳羡茗壶系》的基础上成文的,所以《宜兴甆壶记》《阳羡磁壶赋》同样可以作为研究紫砂壶起源的依据。
第四,吴仕缘何未及时博取功名?都说吴仕自幼警颖,为什么“甫冠”之年未能博取功名?乡试既中解元,为什么又未能联捷进士呢?其间可能有母丧守制的原因,但另有两个原因值得关注:其一,吴仕“禀赋素弱”,时发寒热症,经不起旅途颠簸,以至于“甫冠”之年错失良机。其二,正德二年(1507),吴仕乡试中解元,“试录即以元卷改作程,而文肃公俨是科典试北闱,首程实出其手,兄主北,弟冠南,两京程序,出自一家,一时传为盛事”(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轶闻》)。然正德三年(1508),“刘瑾窃柄,闻俨家多资,遣人啖以美官。俨峻拒之,瑾怒。会大计群吏,中旨罢俨官”(《明史·吴俨传》)。刘瑾专权,吴仕既为俨弟,纵然赴京会试,也是枉然。正德五年(1510),“瑾诛,(俨)复职历礼部左、右侍郎,拜南京礼部尚书”。事发突然,吴仕未能及时参加正德六年(1511)辛未榜会试,所以参加了正德九年(1514)甲戌榜会试,考中进士。
(本文作者系宜兴紫砂文化起源地研究课题组副组长、《洑东村志》主编、宜兴市丁蜀镇洑东中学副校长)